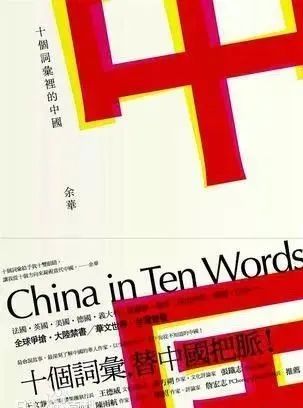2009年,余华在美国期间,受白亚仁邀请前往波姆那学院(Pomona College)讲述当代中国,后撰写了本书,于2010年在法国出版。余华生于1960年4月3日,长于共和国关键期。幼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余华的思维方式,与其说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,不如说是十个词汇中余华,他从:人民、领袖、阅读、写作、鲁迅、差距、革命、草根、山寨、忽悠 十个篇章讲述了那个疯狂年代下自己或他人的故事。 因为成书较早有的篇幅不敢苟同,但仍可揣摩中国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及以后的社会脉搏。值得一读。
「当他人的疼痛成为我自己的疼痛,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,什么是写作。我心想,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,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。所以,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,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。因为中国的疼痛,也是我个人的疼痛。」
- 『从文革开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,「人民」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现实里好像是空的。用现在中国流行的经济术语来说,「人民」只是一个壳资源,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内容用它借壳上市。』
- 「看到我因为止不住的笑而剧烈抖动的肩膀,这几个同学错误地认为我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,他们后来这么说:余华哭得最伤心,他的肩膀抖动得最厉害。」
- 『直到多年后的某一天,我偶尔读到了海涅的诗句:「死亡是凉爽的夜晚」。这个消失已久的童年记忆,在我颤动的心里瞬间回来了。像是刚刚被洗涤过一样,清晰无比地回来了,而且再也不会离我而去。』
- 「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,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。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,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。我觉得,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,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。或者说,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,一条是现实的,另一条是虚构的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,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,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。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,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。」
- 『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,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,「鲁迅先生说」只是一个时代在起哄而已。』
- 『「鲁迅」在中国的命运,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,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,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。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,可以在「鲁迅」里一叶见秋。』
- 「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,鲁迅在我这里,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。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,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,我感慨万端,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,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。」
- 「正是感到自己可以死而无憾,让这个原本胆怯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勇敢的人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,一次对女性成熟乳房的瞬间触及,可以改变一个人。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极端的年代,打架斗殴时我们胆大妄为,渴望女性真实的肉体时我们战战兢兢。」
- 「那个时候,谁要是抢夺到了公章,谁就拥有了真正的权力。可以堂而皇之地发布命令,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财务部门去领取革命经费;可以将自己讨厌的人置于死地,可以将国家的钱用于造反派的革命经费。一切胡作非为,只要写在纸上盖上抢夺来的公章后,立刻就合法化了。」
- 「公正地说,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间,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然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,可是毕竟是在改革之中。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后,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,经济却开始了飞速的发展。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,我们因此置身于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现实里:一边是保守,另一边是激进;一边是政治权力的集中,另一边是经济利益的开放;一边是教条主义,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;一边是循规蹈矩,另一边是放荡不羁……过去的二十年,我们的发展是片面的,不是全面的发展。这样的片面发展,已经伤害到了社会应有的健康。」